经过两年多的等待,弦子终于等来了她起诉央视主持人朱军性骚扰一案的开庭通知。12月2日下午,本案将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庭审。
但这个消息还是让弦子受到震动。因为紧张,担心材料准备不足,她的肠胃炎犯了,疼得胃痉挛。
2018年7月26日凌晨,弦子写下了自己的经历:2014年6月10日,她在央视《艺术人生》栏目组实习,于化妆室采访朱军时,遭对方猥亵数分钟。事后她和老师一起报警,朱军虽也被警方询问,但后来不了了之。
2018年8月,朱军的代理律师以侵犯名誉权为由,将帖子的转发者麦烧告上法庭。弦子被迫应战。9月,弦子以侵犯人格权为由,将朱军也起诉至法院。但此后两年多,两案均无下文,直至最近通知开庭。

弦子的工作照
由于无法采访到被告朱军,这里只能呈现当事人弦子一方的视角。
以下是弦子的自述:
监控录像证明朱军方撒谎
11月23日,我的律师王飞接到法院的开庭通知。我们只有10天的准备时间。我很焦虑,因为紧张,那天我在家哭了一晚上。
就在上个月,我跟律师交谈时,他们还说,这个案子很难开庭。没想到突然接到开庭通知,很多事情都没准备。

12月2日,弦子诉朱军侵犯人格权案将在海淀区人民法院不公开庭审。
2018年7月26日,看到一个姐姐遭遇性骚扰的陈述,我很受触动,为了声援她,我凌晨写下了四年前的遭遇。帖子被麦烧发在微博,得到几位同学的证实,我当年跟他们讲过这件事。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直到8月14日麦烧被威胁退租,8月15日朱军方律师否认事实,以侵犯名誉权为由到法院告了麦烧,我才开始面对法律上的事。
但我们一直没收到朱军方起诉书的副本。9月25日,我和律师向法院提交了起诉朱军侵犯人格权的起诉书。之所以我们起诉朱军的案子会先开庭,法官说,名誉权案的核心事实,要取决于人格权案中的性骚扰是否成立。
民事诉讼的审理期限为六个月。中途我自己去法院催过两次,始终无果。我本以为会一直拖下去。时间隔得太久,这期间,有一年多时间我都没再去管这个事。现在突然通知开庭,我们要熟悉案情,要去阅卷,写质证意见,还有我的那些证人,许多在外地,我担心开庭那天他们不能来。好在他们很支持我,包括我的父母,确定都会出庭作证。一个在外省电视台工作的同学,也请了年假要来北京。
这次开庭,我心理上还是有点回避,担心被问到一些侮辱性的问题,一些让我爸妈难堪的问题,比如性、人品、作风那种羞辱性质的。因为2018年10月第一次庭前会议,他们就是这样做的。
2018年10月庭前会议上,朱军方的律师否认性骚扰的事实,说朱军不认识我,还说我有妄想症。他们提供的证据,是2014年我看病的一条微博截图。我的律师告诉我,这是对方的故意羞辱,目的就是为了让我产生负面情绪,击溃我的意志力。

2018年10月25日,弦子(左)和麦烧。摄影 陈龙
其实我看的病只是神经性皮炎。但2019年1月,我还是去北大六院做了精神鉴定。这个事情也确实对我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,我很害怕开庭。
2018年我的律师王飞递交民事起诉书时,还提交了一份申请书,包含三项申请:调取2014年的报案材料;要求朱军本人到庭;希望本案公开审理。
2019年1月的庭前会议中,我们看到了2014年报案的公安卷宗。卷宗内有我当时的两次笔录,以及我大学老师、大学室友的笔录,详细说了事情经过,还有当时警方去台里调取的监控录像截图。
朱军方的证人包括两个制片人、一个化妆师、一个实习生。那个男实习生,当时和我关系不错,所以我才请他带我去化妆室采访朱军。他们都证明:没有带我去过化妆室,我和朱军不认识,我也没有和朱军单独待在一起的时间。但监控视频证明他们撒了谎。
监控视频对着化妆室门口。视频显示,男实习生带我进了化妆室,然后离开,走廊里陆续有人走过。监控也记录了我出来后,有一个擦嘴的动作。2014年报案时,警察就是指着这个画面说,“这个视频可以作为你被朱军强迫的证据”。这都和我2018年的陈述非常吻合。
当时警察的调查工作还是很细致的。卷宗内有我衣服上的DNA鉴定结果。但当时警察只是去台里给朱军做了笔录,并没有抽取他的血样,所以无法比对。这次,我们申请了重新比对朱军的DNA。
卷宗里也有朱军当时的笔录。笔录里,他没有承认性骚扰,但承认和我共同待在那个房间里,还讲了一下他跟我聊天的内容。这也与他后来说完全不认识我是矛盾的。

见了面,我们都会拥抱一下
这件事情,对我和我的朋友们都产生了很大影响,有的人生方向都被改变了。比如麦烧,她本来在工作,两个月前,她去了英国读书。这次人格权的案子,因为与麦烧无关,所以她不用回来。
2018年曝光朱军性骚扰后,我经常作息不规律,要忙一些网络上、维权上的事情,身体和精神都会受到损害。2019年1月,我被迫去北大六院做了精神鉴定,其实是一个抑郁的状态。在微博上,我经常接到很多女生的求助,那些倾诉也很影响我的情绪。
从2018年到现在,我和我的朋友们接触了很多性侵的案子。我们和当事人从来没有过什么矛盾。一个重要的原因,是我们秉承了两个非常高的社工原则:保密原则、无限容忍原则。
性侵案的当事人一般选择在网上发声的一个很大原因,是Ta没办法在现实生活中取得进展。像上财的案子,她一开始就没办法在学校取得任何进展,去报案也没进展。
性侵案的当事人也有一个共同点,就是在网络求助的时候,Ta们很容易处于一个应激的状态。即使不讨论应对经验的问题,Ta们也很无助,不知所措。这时候,他们非常需要一个支援网络,去应对和处理各种状况。你不能把一个当事人独自丢在互联网上,让Ta自己去跟所有事情对抗,这是很残忍的一件事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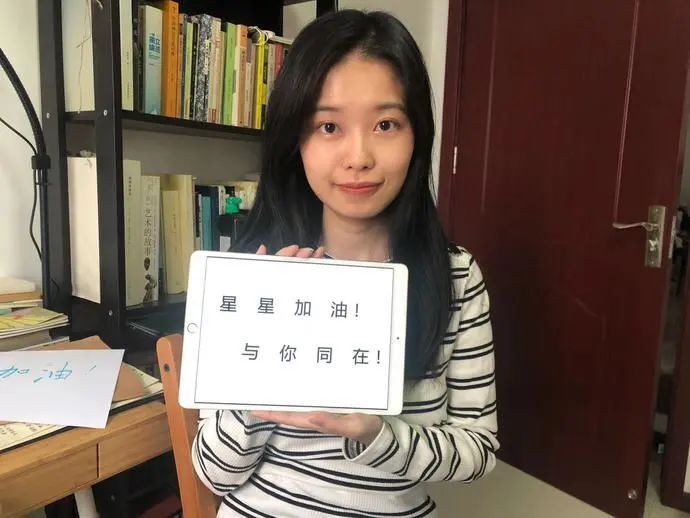
2020年5月,弦子参与联署,呼吁刑法增加利用权势性侵罪。受访者供图
比如,当话题被封的时候,我们怎么帮Ta传递、发声;当我们考虑公共发声的时候,采取什么节奏,在什么节点向大众给出什么信息,我们要采取一个强对抗还是一个软对抗的策略,什么话题上我们要强对抗,什么话题上只需要发出公共倡导就可以——所有这些大家都要商量好,然后一起去做。
Metoo的很多经验,也是逐渐积累起来的。2018年我写下自己的经历,只是为了声援那个姐姐。但麦烧和这个姐姐都是媒体人,因此在公共发言上有着丰富经验,她们告诉我怎么跟媒体交流。直到现在,有些问题我们拿不准的时候,还会去问一下麦烧。如果不是她们,我当时也不知道要做什么、说什么。
正是因为当时接受了别人的帮助,也知道帮助别人很重要,后来你看到一些个案的时候,你就没有办法说“不”。
很多时候,志愿者做的只是一种情绪上的陪伴,尤其在公共发言的时候。相比起来,metoo运动中,很多当事人都比我要坚强得多。我每次跟公安、法院打一次交道,就觉得没命了一样,因为做笔录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二次伤害。最后,这些影响还是要当事人自己去消化。
但是陪伴、共情也是很重要的。去年日本的伊藤诗织来北京,见面后,当她知道是我,我们的第一反应,也是互相拥抱。其他受害者也一样,见面后,我们都会先拥抱一下。
虽然平时网上沟通,大家也知道对方有多么努力,但是在地的支持,在场的陪伴,也很重要。有的案子,虽然大家进不去法院,但是在外面等候,也是一种支持。见面,你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,其实会给你一种力量。一个简单的拥抱,可以替代很多语言上的交流。
所以这一次开庭,我的很多朋友也从外地过来看我。

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。摄影 陈龙
朱军若不到庭,庭审就很荒诞
其实朱军对我而言已经是个很遥远的形象。诉讼阶段,他从来没有出现过。
当年,我们只是要完成电视课的一个作业,老师鼓励我们争取去采访一个主持人。2014年6月10日事发时,在我进入那个房间之前,我都不觉得朱军认识我。
当时朱军已经不主持周播的节目了,前一年也没有主持春晚。我也没想到他有那么大的名气。所以后来反响那么大,大家那么关心他,我就觉得奇怪,因为他也不是追星女孩会注意的那种人。
当时案发后,我把经过告诉了电影史课的Z老师。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有性别意识的人。我第一次接触到女性主义,就是在她的课上。她给我们讲女性主义电影,其中一次是朱迪·福斯特的关于强暴的一个电影,内容是朱迪·福斯特是一个很放荡的女性,她在一次醉酒后被强暴,然后进入司法过程。Z老师告诉我们,哪怕她醉酒,哪怕她很放荡,但被强暴也不是她的错。
Z老师还让每个女生发言,讲自己对性别的不舒服的地方。我就讲,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邻居,老是把我裙子拉起来,说要看我长胖了没有。我就一直记得他那个动作。Z老师当时就非常坚定地说,他这个就是性骚扰,就是在侵犯你。所以Z老师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。第二天是她陪我去羊坊店派出所报的警。
但电视课的M老师,表现完全相反。我报完警回到学校,在寝室睡觉,她跑到寝室,把我从铁架床上摇醒。我当时整个人还是晕的,她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领导,说,“领导,我找到这个学生了,学生一点事都没有”。然后她可能怕我录音,把还穿着睡衣的我叫到外面走廊谈话。她一直说,她的工作关系就落在央视,如果我把事情说出去,她在央视的工作可能保不住,还会被学校老师非议。后来一直到大四毕业,我再也没去见过她。
由此可见,有没有性别意识非常重要。但Z老师当时听了我的遭遇之后,虽然确定我遭遇了性骚扰,也不知道该怎么办,也担心后果。她咨询了她的一个律师朋友,律师的意见是:一定要报警。那个律师说,报警之后,此事就算最后没结果,但起码朱军肯定会被问询,而让朱军被找一次,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震慑。

现在回想起来,幸亏当时有Z老师和那位律师的警惕意识。如果2014年我没有去报警,那么这件事情就永远被掩埋了。而且直到毕业,我的大学班主任也不知道这件事,因为Z老师保护了我的隐私。
事情曝光已过去两年零四个月,我完全没想到会走到今天。当时帖子传播开后,每天有大量工作要做,整个人是被推着走的。对于我来说,很多事情就是必须要去做的。8月份,朱军都把麦烧给告了,难道我不去做证人吗?在这之前,我和麦烧都没见过。很多过程都是偶然推进的。如果现在让我重新做一遍,我也没办法打开上帝视角。
2019年看了卷宗之后,我当然觉得比之前没看卷宗,胜算要大一些。但结果很难预测。
但我觉得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实验。自从2019年民法典将性骚扰的案由列入以后,国内还没有一个实际判决的例子,司法层面还没有形成一个经验。司法实践上面怎么走,法官的判断依据是什么,会不会存在问题,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案子的意义。
我们对朱军的要求,之前只是书面道歉,现在改成公开道歉。此外还要求他给予一定的精神赔偿。接到开庭通知后,我们从海淀区法院得到的消息是,法院拒绝公开庭审,朱军是否到庭也还未知。
之所以不公开庭审,我想可能是因为涉及到2014年警方为什么未予立案的问题。当时,警察来来回回对我说的是:朱军是一个很有社会影响力的人,你要考虑社会正能量,他主持春晚,中国有很多人都喜欢他,他代表一个国家的门面。
但我认为朱军的到庭非常重要。因为事情发生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,朱军既然撒谎了,他必须得接受质询。我希望问他:为什么撒谎?为什么提交了这么多跟监控不符合的证人证词?2018年8月4号为什么要去看我的微博故事?
之前,他的律师已经对一些所谓的证人证词做了公证。我认为那些是假证。如果他不到庭,法官怎么能判呢?朱军本人都不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,法官的判决依据会是什么呢?
所以,如果朱军本人不到庭的话,我就觉得这个过程很荒谬。不管我的结果是输是赢,都不是一个完整的结果。
面对这个案子的开庭,我的内心并不轻松。最近要开庭,我的肠胃炎就又犯了,消化不良,不能吃东西,甚至紧张得胃痉挛,每天喝药。
从2018年开始,我能够公开发声并坚持到现在,离不开大家的支持与声援,也离不开我们彼此的守望共鸣——向历史要答案。并不是说我一定在当下要这个案子的结果。作为最早的性骚扰案由的官司之一,我希望给大家看,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什么,而且我们相信,历史可能会反复,但它一定会往前走。希望有一天,我们会得到一个新的生态。